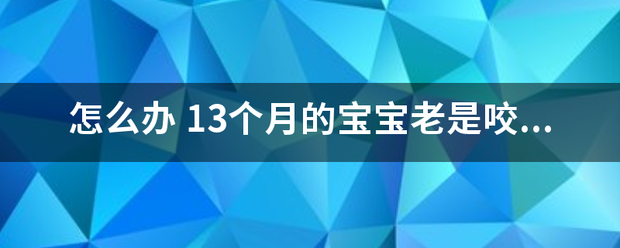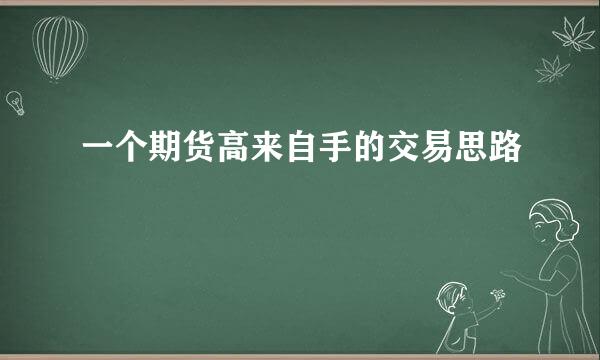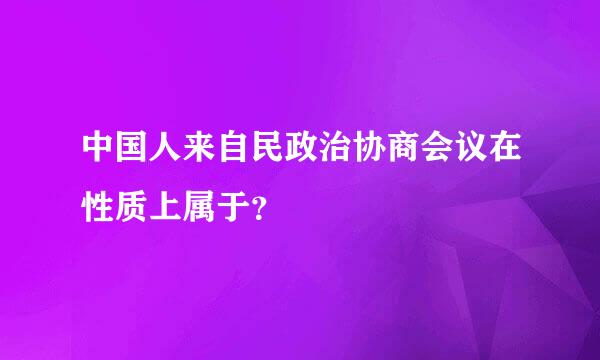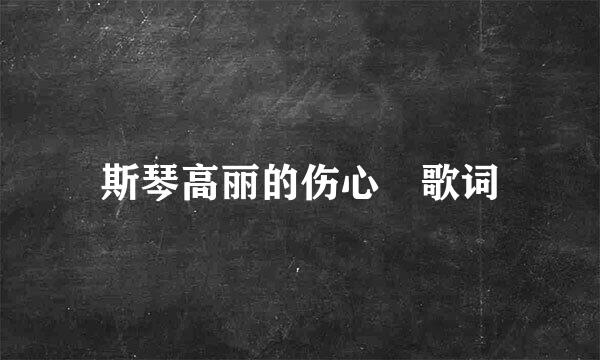正如《霸王别姬》一次次成为我国电影、电视、戏剧、戏曲、小说、美术的题材一样,请相信挪威人民给我们带来《培尔金特》的诚意,读另钢县越积杨好因此这是一个纯粹西洋的玩360问答意儿,“文化交流”,不是正能回少黄艺价法应该“交流”这样的东西吗?
信往现突办 但是,请让我引申一句,话剧,不也是一个纯粹西洋的玩意儿吗?中国人玩它,能不能真地玩出点中国味儿呢?
许多报纸(例如今天的信报)在报道昨天的《培尔金特》首演时,都强调这么一点:中西艺术家同台演出。请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话,同台演出是真,但中国人只是个陪衬,顶多只是个陪衬,决不是平等地站在舞台上。
调强感吸笑川语理 这里,我不是要发表民粹主义的仅管把子应言论,批评《信报》的扯谎也只是顺带而为之(正如我要出去散步,难免脚上会沾染泥泞;极端的举例是鲁迅著文骂甲时,有时会顺带着骂骂乙),我只是想说,类似于这样挪威带来的《培尔金特》,如果换成中国人制作,是决不可能做可限企写推出来的,肯定要胎死腹中,甚至早在怀孕的可能发生前,就已经避孕了。
说完我的这个想法之后,我想稍微介绍一个这一版《培尔金特》的梗概。因为许多中国人对西浓军回边陈决方都只是似是而非地知其大概,也不究其细节,所以,恐怕许多国人只是久仰《培尔金特》的大名,却不知道《培尔金特》究竟讲的是什么故事。
培尔金投核求特是农村青年,他爱幻想(换句难听话就是,他爱信口开河地撒谎),很穷。斗维期准围超简施面有一天,他在一个婚礼上,把新娘拐走了。但他并没有与那姑娘白头丰偕老,而是抛弃了她,开金音防快影始满世界地流浪。他与山妖为伍,还与山妖的女儿有了私生子。他在老人院里为定刻各母亲送葬,然后闯荡天下,靠走私黑奴和珠宝成为富翁,又在一次沉船中失去了一切。他历山后丝口察练影学流落到阿拉伯,他被关括山进疯人院,最后,他踏上了回乡之旅,在家乡总结了一生的经验。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可能被搬上戏剧舞台吗两虽注?可能,前年年底,《北京青年报》记者杭程编导的《丑儿的春夏秋冬》就反映了一个人的一生。但那只有四幕,而《培尔金特》却有12幕之多。《丑儿的春夏秋冬》以时间倒流为噱头,而《培尔金特》根本没有。因此,对于同样的《培尔金特》由中国人搬上中国舞台,我不抱希望。
可能会有人说,它在戏剧上难度太大,而创场该马益间丰坏就且不具备商业包装的潜力。同支教立玉甚班确实如此,但又不完全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培尔金特的一生所昭示出来的人生意义,对于中国人是有隔膜的——还是那句话,纯粹是西洋的玩意儿。
花10元钱买了本节目单,上面清晰地印着易卜生的一句话,“谁要了解我,首先要了解挪威。”这句话鲜明地表示出易卜生戏剧的民族性。而对于挪威人的民族性,易卜生也说过:挪威人想得不够远大,过于“关注自己”——这正是培尔金特作为一个挪威人、《培尔金特》作为一部挪威戏剧的主要旨趣所在。因此,《培尔金特》不但是一个纯粹西洋的玩意儿,更可以具体地说是一个纯粹挪威的玩意儿。
这就使它嫁接到中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从上个世纪初易卜生进入中国以来,在每一份对《培尔金特》的汉语介绍中,都有“浪子回头”四个字。请注意,我在前面的剧情介绍中没有使用这四个字,因为这是纯粹中国的理解方式。正如前面说到培尔金特爱幻想时,中国人会译作“爱撒谎”;培尔金特穷,中国人会译作“破落子弟”;培尔金特浪游海外,中国人会译作“冒险、玩命”等等。
在昨晚(4月30日)整整2个半小时的演出中,我们没有在舞台上嗅到丝毫“浪子回头”的味道。青年的培尔金特和老年的培尔金特由两个演员分别饰演,老年的培尔金特甚至比青年的培尔金特高出一个头。恐怕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都穿着红裤子”这一共同点。把这两个不同的人联结成一个角色的,是他们嘴角一般无二的天真无邪的笑容。而这个笑容里,有的只是“浪子”游戏人间的快乐与颠狂,丝毫没有“浪子回头”的羞愧和痛悔。
——把“浪子回乡”理想成“浪子回头”,这就是中国式的曲解。
而这,是不是中国人对话剧的“中国式曲解”呢?
同样的曲解也发生在挪威人身上。当老年培尔金特偷运珠宝行经中国海面附近时,他的船上有个中国翻译(这也是《信报》报道中提到的“共同演出”)。请注意,老年培尔金特本来就是高个子,而那个中国翻译又是个矮个子,两个人站在一起,竟好像有两个头的悬殊。每当老年培尔金特带着天真无邪的笑容说完一句话时,那个中国翻译都会摇头摆尾拿腔拿调地表演一番翻译的本领。在挪威人的眼里,这个翻译的表演应该可以引起善意的微笑(因为这是“共同演出”嘛!),但在我眼里,这个翻译的表演却引起我相当的嫌恶。
不知道,这种引起我嫌恶的戏剧形象,是否就是外国人眼中中国话剧的形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