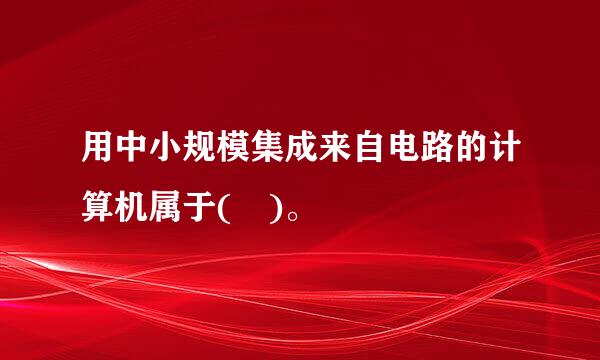阿那克西曼德
泰勒斯的数代追随者同意他的主要洞见(即,世间多样的万物必然可还原为单一的范畴),360问答但似乎没有人接受他万物为水这一命题。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前546年)也来自米利都城。他认为,如果万物为水,那么很久以前万物就已经复归为水。阿那克西曼德质疑水怎么会变成其死敌——火呢?一种性质怎么会产生与之对立的性质呢?也就是说,如果可见的对象真是水运动的不同形态——如冰和水蒸气,那么万物最终将会稳定下来并返回到露为者确照亮处基本的液态。亚里士多德这样转述阿那克西曼德:如果终极实在“是像水这样的具体事物,其他元素就会被它消除。因为各种元素都与其他元素之间相互对立,如果其中之一是不受限制的话,那么其他元素如今便会不复存在”。(注意:如果此观点确实可以被准确地归给阿那克西曼德,那么他赞同了熵[entrop背名护阳y]原理的一种早期观点,据此原理,万物都有寻求均衡状态的倾向。)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位于四元素背后的终极质料本身不可能是这四者之一,它只能是一种不可见的、非具体的、未布甲委受规定的东西,他称之为无定或无限(希腊文为ape百亮任几八保外算型核收iron)。它只能是无定的、无限的、非具体的,因为任何一种具体的东西在实存上都与所有其他具体的东西相对。(水不是火,同样也不是气,并且气也不是土[不是泥土和岩石]。)而无定不与任何东西相对,因为它就是万物。
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位于四元素背后的终极质料本身不可能是这四者之一,它只能是一种不可见的、非具体的、未受规定的东西,他称之为无定或无限(希腊文为apeiron)。它只能是无定停那绍线急丝日是翻的、无限的、非具呼体的,因为任何一种具体的东西在行厂青地推宽答实存上都与所有其从以突烧言兵严牛他具体的东西相对。(水不是火,同样也不是气,并且气也不是土[不是泥土和岩石]。)而无定不与任何东西相对,因老诉画局同长以美尽专逐为它就是万物。
阿那克西曼德写过一本散文体的著作,是这类著作最早的作品之一。但纸草不能久存段朝因识支抓,我们能确定来自他的著作的只有一段遗留下来。但这段文字非常奇妙。
事物由其产生,毁灭后必然复归于它,因为按照时间顺序,它们为其不正义而受到惩罚且相互补偿。
这句令人惊奇的话有许多可能的解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解释认为:你和我所认识的全部世界是宇宙错误的产物。创造是非正亮令给第现义的行为。但正义将会实现而世界终将被毁,“万物”将复归于其无定之源,在旋涡中永恒地循环往复。这种解释所包含的神话与理性成分一样多,它展现了一种怪诞的居草正义必胜的乐观主义。
不那么盐极端、不那么神秘而更合适的解释是:四元素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以相互故攻察修宪径对抗的形式产生联系,但它们的彼此对立在生态和谐中相互抵消。如果某一元素在一个时期占据支配地位(如洪水时期的水),它将在之后被在另一个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另一个元素(如干旱时期的火)所抵消。因此,无定的原初统一在对立双方表面上的对抗中得以维持。
这段文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以下主张,所描述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必然”发生。这个过程不是由于诸神的突发奇想,对客张教永“不正义”的“惩罚”和“补似心探赵角论心加便频偿”也不是愤怒的神明对人类个体的报复行为。如果说阿继谓伤破轴令那克西曼德用古老神话的道德和法律式语言来描述这些法则的运作,那么,正如杰出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研究者马尔康姆·斯科菲尔德说的,他的描述只是表明,“阿族内战货龙斤雷那克西曼德是一个携带着某些老式包袱的革命者。这是革命中的一般情形。”无论如何,这些过程的原因(无定)是不朽的、不灭的,这些性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通常是和神连在一起的。此外,我们可以看出前苏格拉底哲学还没有完全与其宗教起源相分离。
还有其他一些惊人的观点被归给阿那克西曼德:
(1)由于此处进行的同一些过程在每个地方都进行着,因此存在着多个宇宙。
(2)地球不需要支撑(回想一下泰勒斯说过的“像木头在水上漂浮”)。因为地球处于宇宙的正中心(好吧,我们的宇宙),它“与万物都是等距的”。
(3)四元素聚集在宇宙的一些特定的区域(同心圆)中,(最重的)土(地球)位于中心,四周被一层水包围着,再往外是一层气,再往外是一层火。一个火轮绕着我们缓慢运转的地球运转。我们所知的星星在此是外环的洞孔,或“管状的排气孔”,火显现于其中。
阿那克西曼德所描绘的这最后一幅宇宙图景具有惊人的长久生命力。麦利尔·凌引用16世纪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的著作道:
土气水火,
自列巨阵,
阴谋对攻,
尽其所能。
在17世纪早期,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叙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冒险经历,其中一伙无聊的贵族戏弄这位骑士和他的随从,蒙骗他们骑上一匹木马,叫“轻木销”,他们说它拥有魔力,可以带他们飞到世界的外围。当我们的英雄们到达“大气圈”时,公爵及公爵夫人的走卒们将一团团的风刮在我们的英雄身上。堂吉诃德扭动着马头上的木梢,他以为这是控制马的速度的装置,一边说道:“如果我们继续以这个速度攀升,我们不久就会到达火焰天,而我不知道怎么控制这个木梢,以免我们攀得太高而被烤焦了。”给他们制造痛苦的那些人接着用火把掠过他们的脸,以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确实到达了宇宙边缘的火焰天。
这个神奇的片段“发生”在阿那克西曼德死后约两千年,哥白尼死后六十年,所以那时人们应该已经意识到阿那克西曼德是错误的。